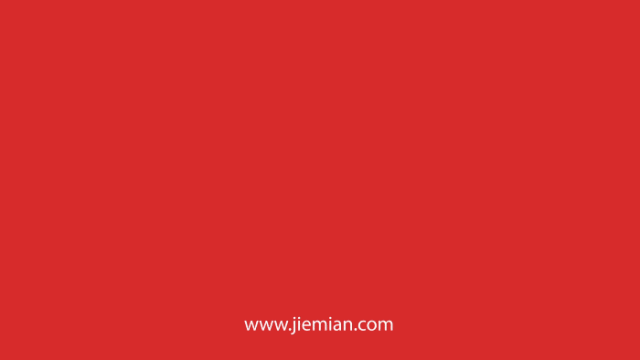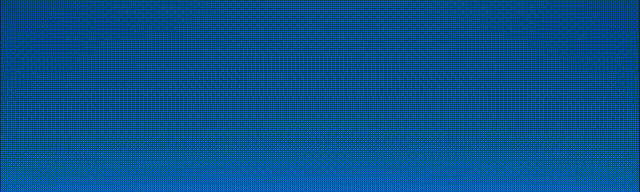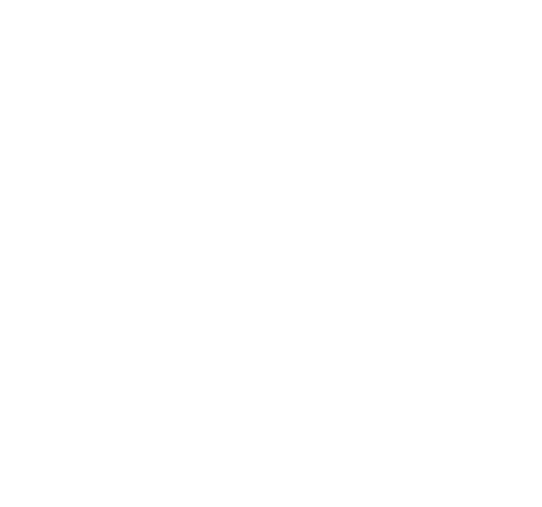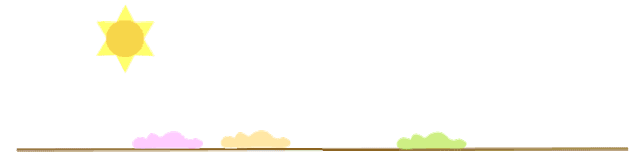一天给3个小孩上6个小时英语课。
这曾是米青的极限。
如今这个数字变成了8个小时。这意味着她要从早上九点一直讲课到下午六点,中间仅有的一小时休息时间里,还要辗转两个校区。
“讲到后面喉咙发干、发痒,最后两节课已经没有力气了,就发题给学生做,让他不懂再问。下班后再也不想说一句话。”然而,下班之后回到宿舍,她还要给学生家长写上课反馈。
助教、老师、还是流水线工人?
米青去年11月加入南京一家知名英语补习机构,任兼职助教,如今已算是一名“老兼职”。年后开始,她的工作强度不断增加,刚开始只是做一些课程调查、给学生默写的助教任务,到现在,主管已经放心地把一些课程教学也交给她。同时她还要带新人,教她们迅速熟悉工作。
刚得知她要去带课的那天,米青的舍友难以置信地瞪着双眼问她,“就你这个英语水平也能去教人家?”
米青并不生气,她自己也怀疑“到底能不能教别人”,毕竟她自己的雅思成绩也才6.5,大学英语六级还是“低分飘过”的。
但她很快就自信起来。
在一般的初高中、雅思托福课之外,机构给基础差的学生专门开设了额外的词汇语法课,兼职助教就负责这类课程。每位助教手里都有一本厚厚的词汇语法书和四套配有解析的阶段测试卷,书里有详尽的教学内容和课后习题,试卷解析把每一题都讲解得一清二楚。
她只需要吃透这本书和这四套卷子,就能不动声色地伪装成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师。上课的内容永远不会超纲,即使穿梭在不同的班级给学生做测试,她也永远只负责那四套卷子。
这让她在舒了一口气的同时又有些泄气,“所以我到底到底算助教还是老师呢?”只有助教的能力,却要承担老师的责任,挂着助教的牌子,却要听上课的学生和家长尊称自己为“老师”。
助教培训守则上的明文规定更加剧了她的不安,“不要说自己是应届毕业生”,“不要随意回答自己不确定或者不该回答的问题”,她掏出一本厚厚的册子指着念,“问题”的后面打着小括号,里面写着“包括薪资和个人隐私”。
入职时,主管曾告诉她隐藏身份的秘诀——穿正式点,别再像个学生似的穿牛仔裤T恤衫,“如果家长问你是不是学生,别回答是,也别回答不是,你就反问对方:‘难道我看着像学生吗?’”这样既不算撒谎深圳职场英语培训课程,又打消了对方的疑虑。
呆的时间长了,越来越驾轻就熟。在米青面前好像有一条工序严谨的流水线,原料处理、装罐、排气、密封……各司其职,她只是众多流水线工人中的一个,永远站在自己的位子上,手脚麻利地工作,看着一批又一批的学生从那头流到这头,在每个老师手上被接手、被加工、被送走,最后离开机构,消失人海,不会在彼此的生活里留下一丝痕迹。
她对此既熟练又不安,渐渐地开始催眠自己:这只是一份机械化工作。
在上海念大三的费新洁也在当地一家补习机构任助教,只是负责批改作业、班级默写、跟家长沟通等辅助工作,并不参与教学,但会完整地陪着学生走完整个课程。
在某次同时带了两个英语班后,她开始察觉出不对劲。
两个完全不同的班级,上课的内容、使用的PPT、课上的练习、课后的作业,甚至讲某个单词时用的梗和笑话,却几乎全都一模一样。“我早上在这个班听A老师讲了一堂课,下午就能在那个班听到B老师讲出复刻版,两位老师可能风格不同,但内容就是大同小异。”
惊讶之后,她渐渐习惯,也开始好奇,为什么老师之间的同步率能这么高?
直到闭着眼睛也能把课讲出来
费新洁没琢磨出的答案,或许能在同事丁灿身上找到,只是此时此刻,丁灿还正在为人生的第一次试讲而焦头烂额。
如果试讲顺利,她将成为费新洁口中众多ABCD老师中的一个。
“试讲”是招聘考核的最后一步,在这之前,老师会参加培训,“熟悉那一套教案,最后流利地讲出来”。培训期间,机构负责食宿,所有人集中在一起练习。
在杭州市富阳区的一个网球会所里,高中部的试讲老师聚集在一个宴会厅中,按学科分组,组与组之间用布隔开。每人可以先自行练习,准备好上课内容,然后轮流到讲台上讲给该组的培训师听,培训师点评,给出修改意见,再喊下一个。得到意见的人先下台修改,改完再站上去,再讲再改,循环往复。
过去的两天里,丁灿把一个十页的PPT背到滚瓜烂熟,翻来覆去讲了十几遍。“就讲其中一个知识点,动词的第三人称单数,就这么一个知识点,十多遍啊!”她激动地强调,苦着脸,“我现在闭着眼也能给你把整个PPT背下来。”
通过不断讲述和重复,直到老师的思维和身体都已将上课的内容死死镶嵌进去,直到就算处于无意识状态,也能流利地讲完一整堂课,“那么效果就达到了。”
更有甚者,一些培训师会要求试讲人写逐字稿,不仅仅是讲义,而是要把上课时所讲的每一个字都写出来、背下来,这样,才能避免即兴发挥可能带来的差错,保证万无一失。而这一切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正式上课之际,让学生和家长认为他们都是经验丰富的老师。
谁也不敢松懈,来的人大多非常想得到这份工作,除了丁灿这样的应届毕业生,转正后的高薪待遇还吸引了不少职场人士来应聘。团建的时候她和周围人聊天,得知组里甚至有人专门从银行辞职来这儿参加考试。
机构的老师也常将此作为激励的号角,“大家放心我们这儿的老师都不差钱,只要你好好干。”在来应聘的学生中也流传着这样一个消息——仅去年一年,他们的校区就创下“四个亿的收入”,绩效排名在所属的全国性教育培训集团中位列第二,前途无限。
“为了工资”
“为了工资”,这是多数大学生选择到课外补习机构工作的重要原因。
今年以来,关于学生减负的文件和措施接连出台,“着力解决中小学生课外负担重问题”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然而,中国的课外补习市场依然朝着越来越火爆的方向狂奔。
仅作为兼职助教的米青,就能利用课余时间拿到150元一天的工资和35元一小时的课时费,在南京这样的二线城市打过多份工,这是她拿过的最高薪水。但对比起280元一小时的授课价格深圳职场英语培训课程,她拿到的辅导费实际不到其中的13%。
机构抽取的87%,要分给电话销售、课程顾问、主管经理、教学研发组,还要用于日常的运转开销。兼职老师只是补习市场利益链条上的一环,在招揽生源上,电话销售和课程顾问同样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电话销售需要通过机构提供的家长的联络方式,一个个地轰炸式推销,课程顾问则需要包装老师身份、推销课程,以达到业绩考核。米青说,有时她觉得累,就坐在办公室听背后桌的一个姑娘打电话,从早打到晚,但基本刚说完“你好我是xxx的……”,就被那头啪地挂断。“这样想,大家都不容易。”
根据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2017年数据,全国基础教育阶段学生课外补习总参与率达47.2%,学生校外教育平均费用约为5616元,全国校外教育行业总体规模达到4580多亿元。全国中小学生在课外补习上平均每周花费5.4小时,时间最长的省份超过每周7小时。
巨额红利催生了巨大的市场,培训机构如春笋般涌现,而辅导教师作为教学和服务的直接提供者,师资的质量和数量都对机构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因此,越来越多的机构开出令人眼红的薪水以争夺优秀师资。
在北京念师范大学的周惠一开始是在师姐的微信朋友圈看到的招聘消息,抱着做兼职挣生活费的心情去了面试,结果一路顺利过关,进入北京一家知名补习机构的听力口语集训营做了老师。
该机构每年寒暑假都会举办冬、夏令营,来的都是些外地的初、高中生,在他们被父母打包送到北京,参加封闭式学习。
在这里,学生每天上四节课,两节听力口语,两节外教课,课后能有半小时的课外活动时间,再加上每天的食宿费,九天为一期,一个学生一期的报名费是4980元。
按照机构开出的基本工资计算,老师每天上两节课,共计三小时,时薪120元,9天全上满也才3240元,税后还剩2600元。
然而,老师们真正拿到的工资却大大超过这个价格。夏令营老师的实际薪酬结构为“底薪+绩效奖金”,绩效奖金与续班率和售课数直接挂钩,即建立在学生口碑基础上的续单和新的售课,以此激励老师留揽更多的生源。
“我们带教的是寒暑假的冬、夏令营,那你想,我们春天和秋天怎么挣钱呢?”周慧问我,接着不紧不慢地报了答案,“就靠着把网课卖给学生啊。”
老师如果能在夏令营期间把1门课卖给1个学生,那他每小时的工资就多涨7块钱。结算工资时就看“收割的人头数”。如果有1个学生买了1门课,就相当于1个人头,买两门课相当于1.5个人头,3门是1.8个,如此按比例类推。通过学生买课的数量推算出“人头数”,再乘以7元,就是最后得到的奖金(每小时)。如果每个学生能买1节课,老师卖给约17个学生即可实现“工资翻倍”。
“现在你知道我们为什么除了上课还要陪孩子了吧。”
周慧参加了两期夏令营,挣了七千多,但她仍不满意,“像我师姐那样的带课达人,带一期课,能挣一万多块钱,我是属于比较弱的。”
“有的老师一个假期光上税就能上万把块。”
而如何卖课,也不大需要老师为此操心,为机构为每个老师都准备了一套面面俱到的流程模板,为了说服学生买课,在为期9天的夏令营里,每一天都有精心设计的“话术”标准。
第一天,要不经意地跟学生透露网课的相关消息;第二天,要询问清楚学生的个人情况,比如之前是否上过相应课程,感觉自己有哪方面不足,希望得到哪些知识的补充等等;到了第三天就开始直接“砸课”。
“砸课”就是把课程“砸”向学生,努力劝说学生买课。常用套路为:我们的课有多好,你有多需要这些课,不买真的很可惜。
第四五六天,重点强力攻克那些有希望买课的学生。最后三天,则针对那些不太可能攻克的学生,再做努力和尝试。
因为套路每年每期都一样,一些之前参加过夏令营的老生也会产生疑惑——为什么这个老师说的话和上个老师说的话一模一样?
这种学生被称为“钉子户”,老师在开班前会吃透学生名单,是否参加过夏令营在名单上都会有记录,而第二天的个人情况询问环节,同样是摸清底细的一步,一旦发现这样的学生,他们会在第三天“砸课”前跟对方旁敲侧击,或拉拢,或叮嘱,之后的“砸课”,也不会太过强硬,避免引起学生反感,从而漏了风声,坏了事。
套路的教学,通通会在开班前的培训期间完成。培训内容包括教书讲课和营销手段,这些也全部统一,强大的教研组早已准备好了详细的教案和话题,只需老师自己下去反复练习。
除此之外,培训师也会教给大家一些讲课小技巧,比如讲一个隐晦的黄色小笑话来带动气氛,正值青春期的学生也确实很吃这一套。
周慧举了个例子:夏令营期间,每个班都会有助教负责拍下学生上课的照片发到微信家长群,及时反馈课上情况。对一些不活跃的班,老师可以问一句:“有人喜欢吃屎吗,喜欢吃屎的人举一下手。”底下就会响起一阵哄笑,有的学生觉得这样很搞笑,就会举手。
“然后助教再把这一幕拍下来发给家长,家长则觉得自己孩子很活跃、很积极。”这一招,在周慧带过的班里,几乎无往不利。
累,很累,忙,超忙
然而,暑假过后,周慧并没有回去上班。
尽管在她看来,这份工作“工资高”,“带教的老师超级棒”,“家长都百分百信任我们”,“和学生相处也很愉快”,但她还是选择了辞职。
因为太累了。
带她的老师进入机构两年,今年27岁,人大博士毕业,在寸土寸金的北京坐拥两套房,是大多数人眼中的人生赢家,也是她心中的榜样。但周慧并不想过这样的生活,在进入夏令营的第二周,她就眼睁睁看着老师被送进了医院,“她的朋友圈都不敢跟爸妈开放,因为里面的照片全是打吊针和加班”。
临近毕业,尽管机构里认识的老师再次打电话过来,但周慧最终还是签了家乡一所公立学校。“待遇确实比不上,贵州也没有北京发达,但我不想年纪轻轻就拿命换钱”。
在东北某市,福建人应羽也面临着本科毕业,却做出了与周慧完全不同的选择。本科学商务英语的她,在春招时几乎投了所有跟英语相关的职位,结果来自深圳的课外教育C机构是第一个通过的,琢磨着在深圳闯两年也不错,她去了面试。
“其实我当时觉得自己表现挺差的,终试的时候有个语法知识点明明就在嘴边,但就是想不起来,结果还稀里糊涂给过了,当场就签了offer。”
“我觉得肯定是太缺人了”,她说。
签字的时候,面试官告诉他们尽快三月底入职,但也不绝对,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安排来填入职日期。她想了想学校那一大堆事情,签了个“四月底之前”,然后在月初就拖了个黑色大箱子,从东北飞到深圳,开始了试用期实习。
在公司承包的15天住宿过期后,她拾掇拾掇,从178元一晚的宾馆逃了出来,蜗居进一家青旅的8人间。这里的住宿费每天只要55元,里面住的全是和她差不多年纪的人,有待两天就走的旅行观光客,也有常住一年、期望在深圳找到未来的求职应届生。
刚开始她并不在乎青旅的条件差,“其实也没啥,这家离公司还近,就是晚上备课的时候得去客厅,周围人都在打游戏、看剧,有点吵”。但很快,大强度的培训和上课让她在晚上回去时疲惫不堪,打开门后还要忍受闹哄哄的环境和气味浑浊的空气,她有些受不了了。
应羽用六个字概括她在补课机构的生活——累,很累,忙,超忙。
虽然只是试用期,但工作与正式员工无差,甚至多了很多的培训课要上,反而更辛苦。因为补课机构的特殊性,他们的双休日安排在周一和周二,但自打上班以来,应羽一次也没有休过周二。
全在备课和刷题中度过。
中考题、高考题、真题、模拟题,一闭眼,她仿佛梦回高三生活,“我觉得我高三都没这么累,考研也没这么累,”说完,又接着摇摇头,“不对,我觉得我这辈子都没这么累过。”
上周五领导突然找到她,说除了周六的一门课,周日还给她安排了三个班,都是一对一,分别上初一、初二和初三。除开第二天本就要上的课和培训,她备课的时间所剩无几,更何况还是三门不同阶段的课。
那天她一直工作到晚上九点,马不停蹄地做笔记,期间一共起身倒了一杯水,上了两趟厕所,吃了同事给的一个法式小面包。晚上蹬着单车回青旅接着备课,平时十分钟的路她蹬了二十分钟,可也完全不觉得饿,“应该是连饿的心思也没了。”
第二天顶着昏沉沉的头去工作,授课对象是个小男生,五年级,活泼可爱的年纪,结果上到两个人都打瞌睡。为了活跃气氛,她问小孩平时喜欢干什么。
“老师你玩吃鸡吗?”小朋友突然来的兴致却让她接不上话。
她不懂吃鸡,别说吃鸡,她甚至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来的第一个月她累到内分泌紊乱,一个月来了两次月经。“我甚至不想跟我男朋友讲话,他每次找我,我看到后要很久很久才记得回复。”
应羽属于半路出家,之前没有经历过任何教师专业培训,一开始她很抗拒上课,觉得自己“什么也不会”,不敢带孩子,更不敢见家长。
深圳的经济高度发展,教育水平超前,来补课的小孩从小就接受良好的教育,家长的学历随便拎一个出来,也比她的高。
隔壁工位的数学老师刚接手一个小孩,家长交完钱,就直接把对孩子的教学计划发了过来。从框架到细节,包括每次课讲什么内容、出什么题、做什么卷子,事无巨细,一一列好。最后在邮件末尾留言:“我不希望打乱您上课的节奏,但希望您能参考我的意见。”
深圳的家长在她心中和面试官一样,慢慢变成学历高、犀利、令人害怕的代名词。“他们根本不是不会教,他们只是没有时间。”
在新浪教育发布的《2017全国中小学生课外培训调查》中,数据显示52%的老师都认为课外培训的作用之一,便是“解决父母没有时间照顾孩子的困扰”。
职场上不会养闲人,试用期内,实习老师一个月上满36小时才有补贴,三个月试用期要上满100小时才能转正。所以她只能一边兢兢业业地备课,一边努力适应这边的生活。
在机构里,授课老师分为三个等级,通过社招进去的、本科大学是“985”“211”的、还有毕业于“双非”大学的,前者等级最高,第二个次之,应羽这种“双非”大学毕业的,属于最低级。老师的待遇根据等级有所差异,而等级又依照任教时间和资质进行评定。
刚开始工作,没有工资,应羽也不好意思问家里多要钱,她靠着微薄的补贴省着过日子。公司在商场,“每顿饭都超贵”,外卖也几乎人均20以上,中午没时间走远了去吃,于是她天天吃商场负一层最便宜的石锅拌饭,18块钱一份,“每顿都吃得干干净净”。
早餐通常在路边便利店买两个包子,后来发现两个包子也吃不饱,就买三个,“但我看人家都买两个,又觉得自己吃得多,”她不好意思地笑笑,“可我真的饿。”
想辞职的念头在她脑海里转了一遍又一遍,坚持不下去的时候,她就找机构的前辈们聊天。给她们做培训的一个老师恰好也是学商务英语出身,老师用过来人的经验劝她,干每一行都不容易,她之前做外贸,每天都要打电话,身上随时背着要完成的单量。
“她跟我讲,在这边套几年工作经验,回家当老师不挺好吗,我想想也是。如果现在放弃了,那之前的辛苦算什么呢。”
虽然累到不行,但她又打心底佩服这样完善健全的培训系统。“我经常觉得自己的思路模模糊糊的,但这里的培训系统真的太好了,教你上什么课,怎么上课,怎么分析孩子,怎么讲题,你只要听就好了,我觉得招的就是我这种特别乖的娃娃,你认认真真地跟着走就好了。”
最后一次采访时正赶上应羽吃完晚饭,急着去备课,软磨硬泡后她答应给出7分钟的时间,7分钟一到,她便急匆匆地开始念叨,“你讲完没,讲完我要去备课了。”
备完课的她还得收拾东西准备第二天搬家,前天晚上10点半,她刚抽出时间去看了一个自如的单间,立马就签了一年。在此之前她物色的多套房子,都因为没来得及去看,就被别人签走了。
接下来的几天里,搬进新家的应羽需要写一封抄送机构80%领导的邮件,是为了请假回到东北参加毕业答辩。
而此时,找到新实习的米青刚跟老板提交了自己的辞职申请,长舒了一口气。
*应受访者要求,本文涉及人物均为化名。